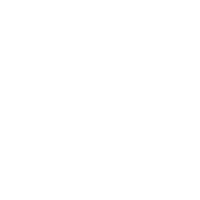麦洁萍
一、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
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对解决未成年人被虐待情况有所改观,关于未成年人被虐待指的是对未成年人有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做出的足以对未成年人实施形式上的躯体和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等[1]。通过相关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未成年人遭受肢体上虐待的发生率高达41.2%~67.3%;遭受情感虐待的发生率在10.6%~67.1%之间[2]。尽管这样的数据可能并不全面,但也凸显了我们需要加强对未成年人这些权益的保障。
当前出现未成年人被虐待的原因,一是部分家长将孩子作为家庭附属品,常对孩子的行为及在校表现做出负面评价,面对“不听话”“反骨”“贪玩”的未成年人常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处理。二是人口流动使得家庭内部隐藏了保姆隐患、父母工作压力、住房压力等问题,使得家庭成员间产生急躁、焦虑等情绪问题,未成年人稍有不慎便是“往枪口上撞”。未成年人被虐待带来的不利后果包括直接导致被虐未成年人身体出现皮肤损伤、毁容、骨折等功能性伤害及对神经系统造成不良影响,也影响未成年人长期发展,表现为被虐未成年人成人后可能会实施与施虐者相同的行为,产生精神扭曲。而要防止这些危害发生更要发挥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事前预防作用。
二、强制报告制度与未成年人司法衔接状况
一是社会知晓度不高。强制报告制度于2020年出台后,检察院、妇联、共青团等部门都加大了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意图让大众知晓并了解强制报告制度。然而就现已发生的案件来说,诸多未成年人被虐待案并没有得到报告主体及时的报告。比如2020年发生的一起虐待未成年人案件:某居委会工作人员在进行家访时发现未成年人身上存在伤痕、母亲存在强行喂饭等异常行为而未报告。这说明这个居委会工作人员并未按要求对强制报告制度进行了解学习。
二是报告主体意愿不强。2021年发生的一起某宾馆接待人员不履行报告义务案件中,宾馆接待人员在发现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入住,且未成年人表现异常的情况下既不进行实名登记也不进行询问,怠于履行强制报告制度,这反映了我国部分报告主体的报告意愿不强烈,因此需要提高报告主体的意愿。同时,在未成年人遭受侵害之后便适用诉讼程序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有着极大的作用,但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对遭受侵害未成年人的前期帮扶,没有形成专门的事前事后心理救济恢复程序,只解决了侵害问题而忽视恢复救济工作。
三、发挥强制报告制度的衔接作用
一是实行严格的从业人员准入机制。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的主体进行入职前犯罪记录查询,包括是否存在性侵记录、犯罪记录指纹、虐待未成年人等行为,通过对从业人员的社会背景进行调查,判断其是否能够胜任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切断未成年人从业入口的潜在隐患并开展定期培训,对从业人员情况进行定期记录,避免出现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同时,设置专门的心理恢复室,通过专业的心理医生为每一个案件发生后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服务,做到按年定期检查以避免出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后因心理问题而产生的自闭、自卑现象。
二是设置完善的侵害识别介入机制。通过运用大数据,在数据平台创设信息公开平台,按照地级市划分区域,将地级市内的区或者县作为一级单位,将所有负有报告义务的部门公布于平台之中,并且要求辖区的相关单位按季度深入了解未成年人的成长状况,按照接触未成年人的距离进行划分,在责任人员内部划分“一级密接”“二级密接”“三级密接”以便于解决出现侵害而互相推诿的现象,保证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林典,卢雨希,王雯斐.小学教师对儿童虐待责任通报的态度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J].少年儿童研究,2019,(12):67-72.
[2]林典.儿童虐待强制责任报告制度之研究——基于台湾地区的政策文本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18,(04):57-63.
作者系广西大学法学院2022级在读硕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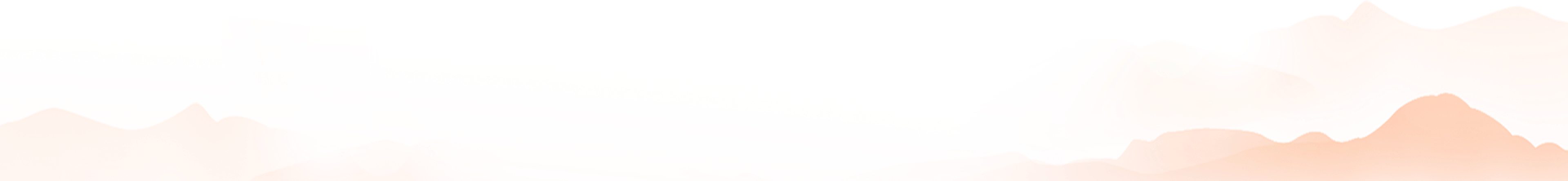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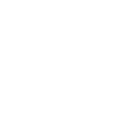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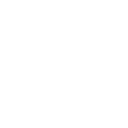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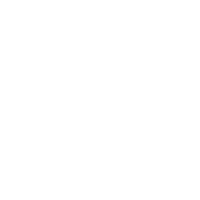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