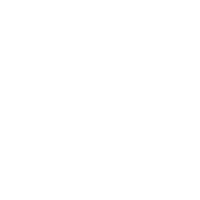□梁爽
若要了解一个人,除了去看他的书柜,就是去看他的冰箱。前者,是精神世界。后者,还是精神世界。因为冰箱里面装什么、装多少、怎么装,一大半也是由精神世界决定的。有的人,常常忍不住买一堆新鲜蔬菜,并不考虑什么时候吃,放烂了再扔掉,循环往复,比如我妈。
于我,有一台大冰箱,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幸福。强迫症最盛的时候,不吃空它是断不能进新东西的。稍微理智一些的时候,里面不能有超过一星期用不掉的新鲜食材。这意味着,我七八天买一回菜,一次用不了二十块钱。但我妈常常不知道想吃什么,看见什么就买,买完了没空吃,等有空了又突然想吃别的那一群人的代表。所以每逢妈妈前来看望儿子时,打开我的冰箱,总有一种想把它塞满的冲动,觉得我这不像过日子。我也总是严词拒绝,好不容易吃空了些,真不能再装了。等一盒酸豆角、两罐炸酱放进去,招待我的除了一桌好饭,还有一句“早知你这么浪费,不如买个小冰箱”。
浪费吗?不浪费,小了就装不下,大的才有空气感。就比如画画吧,总得留点儿白。就比如写东西吧,总得起来喝口水,上一回洗手间,再回来坐下。就算不画不写,只以肉身行走坐卧,也难以想象七窍壅塞,内脏之间没有空隙。冰箱亦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腔体。缝隙,很重要。流通,很重要。它是消除一切焦虑的前提。
“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周的智慧,流传下来,常常被误解。费这么多笔墨讲一个故事,真不是为了教人解牛,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机会解牛。那是干吗呢?当然是传授养生之道,消除内心焦虑,为了一辈子活得自在顺畅。尤其到了关键点上,“见其难为”,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
旧时北方寒冷的冬季,大人们常把需要冷藏的吃食直接挂在窗外。大自然成了天然的冰箱。只要窗把手还受得住,只要窗檐还有一丝空地儿,都会被榨干用净。那时候,冰箱是公共空间。一日比一日薄得透亮的塑料袋,显出里面支棱的排骨或带鱼尖尖的嘴,或者奶油冰棍儿包装纸的锯齿边缘。小孩子隔着窗玻璃看着,一天比一天更馋。
时至今日,冰箱依然保留了某种展示的属性。就像有人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冰箱贴,有些人干脆拿冰箱当留言板,上面磁吸着一个新学的食谱、总也勾不完的待办事项,便条上写着“我爱你”或者“交电费”,或是一首诗。这大概是一种把书柜搬到冰箱上的行为。当然,如果这么写了,这几样东西最好开门就有,否则存在诱骗之嫌。
如果没有,最好能提供一些补救措施。尤其是本来预备妥当,莫名其妙又没了的。像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用矫情的分行写作告诉某个迟起的人,“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能好好说话吗?你留着的早餐被我吃了。但我十分开心,你也十分开心。这就够了。
这哪里是请求原谅,分明是暗自炫耀。毕竟,当代冰箱已经是私密的领地。翻来就吃显然有失礼貌,除非关系足够熟稔亲密。如果冰箱也有心智,怕是要为这层逻辑打一个激灵。你听那突然紧起来的一阵嗡嗡声,或许就是它在说,受不了受不了。
机器按程序工作,唯有人类的想法每每不循常理,偶尔妙不可言。1948年,美国记者阿特·布赫瓦尔德前往巴黎拜访海明威,同行的一位朋友认真请教,“如果想成为作家,需要做什么?”海明威的回答是:“首先,你得给冰箱除霜。”这真正是一个好活计,冷静,治愈。写不出来别硬写,读不下去就放下,且松松快快过一过生活。
“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什么好吃的、好看的、梦寐不忘的,也不必尽数收入囊中。人间不是宝绘堂,还是掂量着办,负担最小,而满足感放大。尤其当我想到,仅仅是打开冰箱门,我召唤出的光就比18世纪大多数家庭享受到的总量还多,快乐也随之亮了几瓦。
(作者系《中国审计报》編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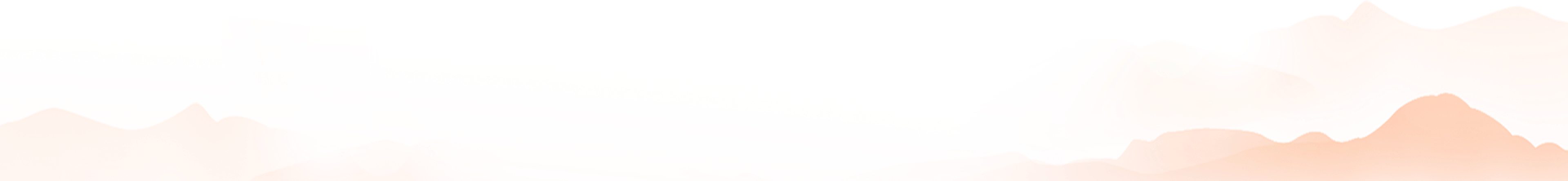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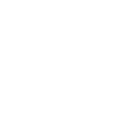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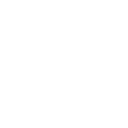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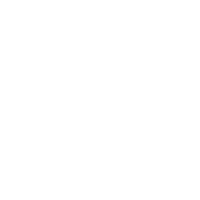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